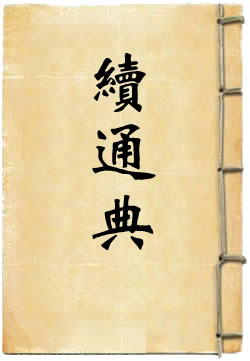●卷三十一
○认族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符合,此习自古已然。李唐自以为出老子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并以《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郭崇韬以汾阳王为远祖,西征日,路过河中,祭汾阳墓,哭甚哀。南唐王李以唐吴王孙有功,子岘为相,遂以吴王为祖,自岘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为光宠者也。然狄武襄官枢密使,有以狄梁公画像及诰敕来献者,武襄曰:“一时遭际,安敢远附梁公耶?”其见卓矣!又有本非同姓,而强为联宗者。《北史。唐瑾传》:周文赐瑾姓宇文氏,燕公于谨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庶子孙承其馀论,有益义方。”周文乃更赐瑾姓纽于氏,谨遂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此则非同姓而认族,实为千古所未有。然于谨以其家法而欲师之,非后世依光附势者之为也。《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朴与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为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传》:侯景以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说:罗绍威为节度使,以罗隐名士,拜之为叔,赠遗甚厚。《宋史》:蔡京于蔡襄虽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谓襄族弟。此犹第以门望相附,不专为势利起见。(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他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乃请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附门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晋书》:孙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厮役也,为梁制局监,遂附之。《旧唐书》:李义甫既贵,自言本出自赵郡,始与诸李序昭穆,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弟子礼,谓之五父。《宋史》:史正志与史浩异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则专以权势夤缘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嶷尊蔡京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见,嶷遽曰:“大误!公乃叔祖,公子乃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温公琐语》:张洎为举人时,张亻必已通显,洎每求见,称侄孙。既及第,称侄。及秉政,则并以庶僚遇亻必矣。此更势利之最可笑者也。○同姓为婚《史记》帝尧与舜皆黄帝之后,计其世数,则尧之女于舜为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时虽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邃古之传讹,《史记》不察,遂笔之于书,未可尽信也。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时最多。《论语》:鲁昭公娶于吴,同姓,谓之吴孟子固己。《国语》:富辰谏襄王,有曰:“聃由郑姬。”注:聃,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郑女为夫人。《左传》: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又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亦姬也。郑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于今。”齐崔杼见棠姜美,谓姜之弟东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注:谓同姜姓也。子产谓叔向曰:“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今晋君内有四姬,其病无乃是乎?”庆舍以女妻卢蒲癸,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独焉避之?”庆氏、卢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时乱俗也。汉以后此事渐少。《汉书》:王莽以姚、妫、陈、田、王氏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然《王传》:孙咸有女为王莽妻,号宜春氏。注张晏曰:莽讳娶同姓,故以侯邑为氏。师古曰:莽以己与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别,故娶之。然虽不同宗,终属同姓也。《魏志》: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刘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丧乱前事一切勿问。(《晋书。刘颂传》:颂嫁女陈峤,峤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而姓陈。其友尝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叶,而世皆为婚,律不禁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当世大儒,而为子纳司空王沉女,以姓同而源异也。《晋书。载记》:刘聪欲纳太保刘殷女,以问刘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李弘亦引王基为子娶王沉女为证,遂纳之。刘曜妻刘氏将死,谓曜曰:“妾叔父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乃娶皑女为皇后。按聪与曜皆匈奴后,其娶刘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属同姓,非礼也。北魏本无同姓为婚之禁,至考文帝始禁之,诏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皇运初基,未遑厘改,自今悉行禁绝,有犯者以不道论。”《唐书》:李光进之母李氏。
○交婚《魏书》:慕容元真以妹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请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为妯娌《北史》:崔长谦幼聪敏,卢尚之欲以女妻之。崔忄又为长谦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为娣姒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为婚《南史。韦放传》: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适率子。《北史》:崔浩女为尚书卢遐妻,浩弟恬女为王慧龙妻。二女俱有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慧龙子宝兴将娶卢女,浩为撰仪,躬至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
○劫婚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妇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皆可看新妇。固系陋习,然自六朝来已然。《南史。徐ゼ传》: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唐李涪《刊误》云:婚礼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通谓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故,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则此习由来久矣。《汇书》:近时娶妇,以红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议曰: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合卺复乘。是蒙首之法,亦相传已久,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今则为通行之礼耳。
○冥婚《周礼》地官有嫁殇之禁。注谓生时非夫妇,死而葬相从者。曹操幼子仓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然终聘甄氏亡女与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北史。穆崇传》:崇玄孙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中宗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萧至忠传》:韦庶人为亡弟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建宁王琰传》: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亡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经之甚者。《五代史》:郑余庆作书仪,以冥配为定制。唐明宗深识其非,有诏删正。然康誉之《咋梦录》: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而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者就男墓设酒果,以合婚。二座相并,各立一小幡,奠毕,二幡微动,若相就。其有不动者,则以为不喜也。两家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给。《元史》:郭三从军死,其妻杨氏守节,舅念其子,不忍使鳏居地下,欲聘邻家亡女合葬之,杨氏遂自经死。则元时犹有冥婚之俗。而杨用修《丹铅录》亦云:今民间犹有行焉而无禁也。然则前朝尚有之矣。
《魏书。高允传》: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凭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莫此为甚。然则北魏时又有所谓魂人者。
○撒帐《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
○拜堂新婚之三日,妇见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闻见记》: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拜堂之仪,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却扇,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段修,无拜堂之仪。”今上,谓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来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枣栗段修见舅姑,即今俗所谓拜堂也。乃又云无拜堂之仪,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
○脱袜登席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也,袜去,故行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A11M]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谓有足疾也,[A11M],呕也。注又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屦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屦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三国时,吴贺邵美容止,坐常着袜。则是时家居亦多有不袜者。)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是时藩国朝贺其王尚皆跣,故诏改之,以杀其礼。)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阎若璩据此语,谓古惟燕饮始跣而为欢,祭则不跣也。按《韩诗》不脱屦而即席,谓之礼;跣而上坐,谓之燕。则古人行礼尚着屦,燕乃跣袜,阎说盖本此。)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即绝恒礼,凡屦行者应皆跣袜。(盖是时庙祭有不跣袜者,故申禁之。)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登,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着靴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唐书》皇甫以故缯给边兵,军士焚之。裴度奏其事,在宪宗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府物,坚韧可用。”韦斌每朝会,不敢离立,尝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几没靴。崔戎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单骑遁去。温造节度兴元,杀倡乱者八百人,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乃免之。是唐时已多着靴。欧阳公《归田录》:和凝以三千钱买靴,问冯道靴价若干,道举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仆。道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证。宋以后,则朝靴且形之歌咏,而《朱文公家礼》内“冠仪”一条,并有衤阑衫带靴之制,则靴固久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赵武灵王始用之,然秦、汉、魏、晋尚罕有着靴者。《晋书。儒林刘兆传》: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问刘延世。又《毛宝传》: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此盖骑者用之。靴字从革,盖皆皮为之,便于骑也。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有告讦者,辄置靴中不视。梁王俭宴客乐游苑,萧琛着虎皮靴,直造其坐。陈徐陵为吏部,陈暄袍拂髁,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而已。其时多着屐。齐明帝辅政时,百官皆脱屐到席,蔡约独蹑屐不改,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固无论于着靴也。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长安,夫妻常卖靴自给。北齐娄太后病,童谣有“紫纟延靴”之语。徐之才曰:“紫者,此下丝,纟延者,熟当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时,杨逃出,遗一靴。《任城王氵皆传》:有妇入浣衣,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琅阝琊王俨被害,亦不脱靴而埋之。及北齐亡后,嫔妃入周,亦以卖靴为业。是北朝着靴,累代盛行。盖自刘、石之乱,继以燕、秦、元魏、齐、周,各从其本俗,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寻为朝制耳。风会所趋,随时而变。古以脱袜为敬,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又其后则不脱履,最后则靴为朝服,而履反为亵服。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反为大不敬,更无论于跣而见也。或疑古人脱袜而登,近于裸亵。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颇斑斓可爱。想古人邪幅在下,亦复如是,则亦未为污渎也。按《明史》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黑袜履,惟公服则用皂靴,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庶人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翁;北地苦寒,许穿牛皮直缝靴。
○弓足妇女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又唐诗:“两足白如霜,临流濯素足。”陶南村谓唐人题咏甚多,略不言纤小。又《郡阁雅谈》引五代刘克明《蒲鞋》诗云「“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鞋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谓此诗通首咏妇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纤之状,则是时尚未缠足。并引《太平御览》云:昔制履,妇人圆头,男子方头(见《宋书。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圆为别也。胡应麟因之,力主起于唐末五代之说,谓古人言妇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纤腰而不言纤足。古人风俗如堕马、愁眉等妆,史传皆不绝书,而足独无明文,李白至以素足咏女子,则唐时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于五代之说也。然伊世珍《郎记》谓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长仅三寸。《诗话总龟》亦载明皇自蜀回,作杨妃所遗罗袜铭,曰:“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纤圆,恰似同衾见时节。方知清梦事非虚,暗引相思几时歇。”又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韩《さ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杨用修因之,并引六朝《双行缠》诗,所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以为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句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纟徒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锐言之也。则缠足之风,战国已有之。高江村《天禄识余》亦祖其说,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之步步生莲花,然石崇屑沉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已先之。而《史记》并有“利屣”之语,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于秦、汉之说也。是二说固皆有所据,然《郎记》及《诗话总龟》所云,恐系后人附会之词。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即杜牧诗之“尺减四分”,韩诗之“六寸肤圆”,亦尚未纤小也。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不裹。滇黔之倮苗、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谈》)。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凤染指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杂识》: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直至退甲,方渐失之。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
○簪花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其见于诗歌,如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醉插茱萸来未尽”,杜牧之“菊花须插满头归”,邵康节“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圣俞《谢通判太博惠庭花》诗“欲插为之醉,惭但渐发星星”,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云:“头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陈无已”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山谷词”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陆放翁诗”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类,不一而足。按《羯鼓录》:汝阳王随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时已簪花也。宋真宗将东封,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先宣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陈去所戴者,亲以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又《盛事美谈》记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上特顾晁迥、钱文僖,各赐一朵。又故事,惟亲王宰臣则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为晁迥戴花,观者荣之。又《宋稗类编》记寇准侍宴,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曰:”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沈括已韩魏公镇扬州,适芍药生金缠腰四朵,延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开宴,各簪一枝,后四人俱为相。《司马温公家传》:公年二十登第,闻喜宴,独不簪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史》:颜师鲁充显仁后遗留使,至金,力辞簪花听乐。莫充贺金正旦使,赐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又陈随隐记:孟冬时享驾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薄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杨诚斋诗:”赐花新剪茜香罗,遍乌纱未觉多。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则并簪剪彩之花矣。《古今诗话》:孙周翰童时,侍郡侯宴,适座客簪花,郡侯出对曰:”口吹杨叶成新曲。“韩对曰:”头戴花枝学后生。“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金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又元遗山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插花归去蜂随帽。“《漱石闲谈》记,明成祖时迎春,监生当代为簪花,众皆畏缩。有邵者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傅维麟《明书》: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导。则金、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
○妇人拜《礼》:妇人吉拜〔事〕,虽君赐肃拜。肃拜者,《周礼》太祝九拜之一。郑注谓俯下手,如今之扌壹。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扌壹。肃拜如扌壹,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诸家之说纷纷。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战国策》苏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此畏惧之至,过为加礼,故特记史。《史记》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此亦特为加礼,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诏曰: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亻免伏如男子。欲妇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诏书,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说也。《清波杂志》则谓古之男女皆跪。古诗曰“长跪问故夫”是也。罗《鹤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古乐府所谓“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说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为跪,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诗“伸腰跪拜”正是实事。引身长跪,拢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状。《朱子语录》所谓直身长跪,拜时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肃拜。妇人首饰甚多,自难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时,妇人有跪拜之礼也。迨后坐用床榻,则妇人之跪不便,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故不令拜跪,究属臆说也。(《宋史。王贻孙传》:太祖尝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贻孙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赵甚重之。亦见《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必兼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以古诗“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自可了然也。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之状,此亦有所本。宋太祖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肃太后垂帘,欲被兖冕,亲祠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当为男子拜乎?”议遂止。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为稽首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虚坐之势。然则拳曲虚坐,亦自宋时已如此也。惟是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隋时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误》云:今郊天祭地,止于再拜,乃妇谒姑嫜,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姑嫜跪而受之,当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则唐时妇初见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状,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盖家庭则舅姑,宫廷则君后,皆属至尊,自宜加礼,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则仍肃拜也。
○古人跪坐相类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与不着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近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谓盘膝坐。则又误。盘膝坐则向栩、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
○高坐缘起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县,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学攵,登榻坐,学攵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钅至《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拜,虽臣之于君,亦只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顿首,则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礼。至后周天元帝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于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误》谓,郊天祭地,止于再拜。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子于父母亦四拜礼。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按《乐记》有”百拜“之语。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繁数如此。注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
○润笔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也。然《北史》袁聿修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敛缣帛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诏许之。则又在郑译之前。故洪容斋谓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而王《野客丛书》并谓: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其见于史书及载记者,唐《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故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甚著书,惟应人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获金帛。柳公权善书,公卿贶遗巨万。主藏奴盗其所藏怀盂一箧,识如故。奴妄言叵测。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惟笔砚自秘之。李商隐记刘义持韩愈金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如与刘君为寿。”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为裴度作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又柳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尝诵其送人诗“薄糜不继袄不暖,饥肠犹作钟球鸣”之句,谓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粮方也。”《明史。李东阳传》:东阳谢事后,颇清窘,有求碑志者,东阳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亦可见其清节矣。然利之所在,习俗渐趋于陋。唐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侯鲭录》记王仲舒为郎中,谓马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册一帙,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事见《戒庵漫笔》。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也。
○避讳避讳本周制,《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是也。然周公制礼时,恐尚未有此。虽《金》有“以旦代某”之语,然《金》之真伪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诗曰“克昌厥后”,戒农官之诗曰“骏发尔私”,皆直犯文、武之名。虽曰临文不讳,然临文者但读古书遇应讳之字不必讳耳,非谓自撰文词亦不必讳也。而周初之诗如此,则知避讳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盖起于东周之初。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鲁以献武废具敖。考数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时已有避讳之例,岂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时尚未有禁,及后避讳法行,乃不得不废官及山川名耳。孔门以后,习礼者益加讲求,如《礼记》所载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类,可谓情义兼尽。然朝廷之上,犹未有听以私讳避官名之制。故汉时孔安国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讳,不肯连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无私讳驳之,遂不许。至晋江统疏曰:“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许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选之例。但身没之后,子孙难以称其位号,宜听其一并回避。”诏从之。则是时已著为令甲矣。《宋史。贾黯传》:律载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有罪。则并有不避讳而议罪之律矣。雍熙中,诏除官若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则更有因私讳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观之,盖自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讳著为律文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范蔚宗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陈书》孙奂欲以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曰:“廓父名泰,不可为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萧俨拜太仆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卫率。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谓其父名少康,当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国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馆,以父名昭恳辞,乃改集贤院。吕希纯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讳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张亢授庆州,亢以父名余庆,力辞,不许。李若拙授太子赞善,若拙以父名光赞辞,不许避者。)晋咸和中, 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舒以父名会,不拜,诏改会为郐。后唐以郭崇韬父名宏,乃改宏文馆为崇文馆。宋慕容延钊父名章,太祖乃授廷钊同中书门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吴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程元凤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此因私讳而并为改官名者也。
张世南《游宦记闻》云:生曰名,死曰讳,世俗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是称生人亦曰讳,乃不祥之甚也。今时俗口语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检。
○嫌名嫌名不讳,韩昌黎《讳辨》已详论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为内,已著为令。至唐时讳嫌名者更多,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议者引《礼》折之,始受。萧复为晋王行军长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为统军长史。则朝廷之上且为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贺应进士举,当时流俗以其父名晋,遂同声訾议也。然《唐书》卫洙为郑颍观察使,洙以官号内有一字与臣家讳同,欲乞改授。诏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李奚传》:宦者摘奚疏中语犯顺宗嫌名,奚奏曰:“《礼》不讳嫌名。”不坐。则唐律本有嫌名不讳之条。
○二名《旧唐书》:太宗诏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自今官员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是太宗之诏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虽不连属者亦避之。避世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避民为人,如民部改为户部,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盖世南没于太宗时,正遵奉诏旨故耳。其后李世但称李,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司马迁之父名谈,故《史记》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赵谈改作赵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庙讳,而但称其字者。如北齐以高欢先世有名泰者,故于宇文泰但称其小字黑獭;有名隐者,故于赵隐但称其字彦深。唐讳虎,故于石虎但称其字季龙;讳渊,故于刘渊但称其字元海,邓渊但称其字彦海;讳治,故于长孙稚但称其字承业(此并讳嫌名)是也。有以讳而改用文义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汉明帝讳庄,而东汉人凡旧书所有庄字皆改为严,以鲁庄公为严公,楚庄王为严王,庄助、庄子陵皆改姓为严。王羲之之先讳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时益踵其法,如改虎为武,渊为泉,又为深,世为代,民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萧渊明为深明,李安民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长孙稚名为幼,甚而别称虎曰猛兽,曰于菟。(《隋书》赵仲卿为政猛,时人谓之猛兽。《北史》又云:时人谓之于菟。)此皆以文义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刘臻好食蚬,以父名显,乃改呼曰扁螺。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殊觉可笑。东坡以其先讳序,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则不免窒碍,近世缺点画之法,最为简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礼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此但讳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为别也。然《礼》又云:既卒哭,以木铎犭旬,曰舍故而讳新。杜预注《左传》引之,以为舍亲尽之祖,而讳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则讳当及五世矣。《吴志》:张昭著论,亦引逮事之义,谓六世亲属竭矣,则不必讳。周穆王名满,而后有王孙满;厉王名胡,而庄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讳及五世之证,则避私讳当以五世为断。(唐庙制:已祧不讳。故高宗讳治,而韩昌黎《湖州上表》内“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盖宪宗时已祧高宗也。)
○觌面犯讳六朝时最重犯讳。《南史》谢凤之子超宗,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辄走匿不敢对。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卿书何如虔公书?”答曰:“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退。盖各触父讳故也。殷钧尚永兴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满壁书其父睿名。钧辄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自称“触触生”。虽为当世所笑,然其时避讳之严,大概如此。董《燕闲常谈》云:许将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钱若干,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许厉声曰:“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其人方悟。元绛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挥。”元拱手曰:“元绛何尝指挥?”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觌面犯讳,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
更新至 · ●卷四十三
2025-12-10网友评论
“赵翼”相关作品
-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
《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答桓南郡明报应论》的简称。东晋释 慧远撰。为中国早期佛教阐述因果报应论的文章。强调 因果报应是“自然感应”、“必然之数”,是人生的必然规 律,“虽欲逃之,其可得乎?”认为灵魂(神)是因果报应 的主体承受者,由地、水、火、风“四大”结成的形体可不 断生灭,而受报的主体则是不灭的。指出因果报应由人 们的无明和贪爱所引起,是自作自受,无外来的主宰: “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本以情感而应自 来,岂有幽司?”认为超脱因果报应支配的关键在于反 心,反心就是“冥神”,即停止精神活动,求得精神解脱。 此文载《弘明集》卷五。
慧远 · 著 -
沙门不敬王者论
《沙门不敬王者论》全一卷。略称不敬王者论。东晋慧远(334~416)撰。论述沙门不须礼敬王侯之理由。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弘明集卷五。东晋时,鉴于太尉桓玄之压迫佛教,佛教教团乃发表宣言,认为佛教教团应处于国家权力之外,然同时代之车骑将军庾冰则主张佛教沙门应对王者礼敬。安帝之际,桓玄支持庾冰之论,谓佛教教团应从属于国家权力之下。本书作者则本佛教徒之立场,主张沙门不必礼拜帝王。在印度佛教之理念中,在法(真理)之前,不论帝王或沙门一律平等;法即是不变之真理。此一观念于佛教传入我国后,因佛教势力之逐渐强大,而形成国家权力与佛教理想之冲突。作者于本书序论中叙述其撰述理由,其次再从第一‘在家’、第二‘出家’两篇中论述佛教出家之本质,强调出家者之生活必然超越世俗生活。第三论‘求宗不顺化’,谓求佛道者,不应随顺世俗,而须否定世俗之生活。第四论‘体极不兼应’,谓体得佛法者,不应再顺应世俗。第五论‘形尽神不灭’,谓肉体终将一死,而精神永不灭绝。于本书中,显示佛道之追求者坚守宗教真理,对于世俗之权威丝毫不让步,然此一思想随时代之变迁而逐渐步上妥协迎合之道。唐朝彦悰根据本书而将历代之不拜论集录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一书,共六卷
慧远 · 著 -
九转灵砂大丹
《九转灵砂大丹》九转灵砂大丹,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言炼制九转灵砂大丹之法。先作准备:将水银、硫黄炒研成青金头末,造炉铸鼎,升砂煮砂,用花银作银珠子。准备完毕开始炼九转丹。第一转先以银珠与煮过灵砂配合成药头,人炉固济,升火伏炼而得初真丹。然后以前转所炼丹药为料,再加砂添汞烧炼。依次得到第二转正阳丹、三转绝真丹、四转灵妙丹、五转水仙丹、六转通玄丹、七转宝神丹、八转神宝丹、九转登真丹。书中详载各转所需药物及入药烧炼方法。据称从第五转起,所得丹药可点汞成金。至九转丹成,服之可以升仙。
佚名 · 著 -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
《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颂注,金朝道士默然子刘通微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以五言颂诗注解《清静经》。注文融合道禅,以澄心遣欲,清静常寂为宗旨。劝人去贪嗔痴,修戒定慧,则六欲不生。法界宽广。
刘通微 · 著 -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
《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凡三十卷。唐代菩提流志译。又作不空罥索经。说不空罥索观世音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分七十八品。今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不空罥索咒经(隋代阇那崛多译)、不空罥索神咒心经(唐代玄奘译)、不空罥索咒心经(菩提流志译)、圣观自在菩萨不空王秘密心陀罗尼经(宋代施护译)等,皆出自本经卷一母陀罗尼真言序品。不空罥索陀罗尼仪轨经二卷(唐代阿目佉译)则出自本经之母陀罗尼真言序品、秘密心真品、秘密成就真言品等。又本经经文与大日经相类处颇多,由此推知,大日经之编纂与本经亦有关联。
佚名 · 著 -
静庵文集
《静庵文集》近代王国维诗文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自辑其光绪三十至三十一年所著哲学、教育等论文十二篇及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一年诗五十首而成。内容较多介绍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据批判程朱理学,认为理只有理性和理由二义,皆主观上之物。《红楼梦评论》为以哲学观点评论文学作品的开端,对后来的《红楼梦》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区别,持超功利主义艺术观。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使人求得暂时的解脱。此论集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清末曾列为禁书。光绪三十一年出版于上海。收入商务印书馆《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王国维 · 著 -
太上洞神五星赞
《太上洞神五星赞》太上洞神五星赞,原题张平子(东汉张衡)撰,疑为南北朝或隋唐道士所作。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赞颂类。本篇为天文星占之书,观察木、火、水、金、土五星在二十八宿中运行情况,以占验灾祥吉凶。又叙述禳解灾祸之法,有施舍、修德、设醮,转诵金简玉经等方法,谓行之可逢凶化吉。经名「五星赞」,应为「五星占」之误。
佚名 · 著 -
二程外书
《二程外书》南宋理学家朱熹编纂的程顥、程颐讲学语录。12卷。 成书于乾道癸巳 (1173年) 元月。《二程遗书》 皆门人当时记录,而于二程之语则有所遗漏,朱熹于是取诸人集录参照删削,得此12篇。凡采朱光庭、罗从彦等7家所录,又胡安国、游酢家本及建阳大全集印本3家,又传闻杂记,共152条,以补《遗书》所未备,均以 “拾遗”标目。自谓取材较杂,真伪相间,不如《遗书》之精审,故称为《外书》。此书虽“记录未精,语意不圆”,但“其言足以警切学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2) 。认为 “穷理、尽性、至命,一事也,才穷理便尽性,尽性便尽命”(《二程外书》卷11)。主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学本” (同书卷1) 。是研究二程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收录。另有《河南程氏全书》,《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洪氏唐石经馆丛书》、《四部备要》收录《河南程氏外书》。
朱熹 · 著 -
道德真经颂
《道德真经颂》道教经籍。题“茅山蒋融庵撰”。分81章,以七言诗颂解《道德经》,但不引原文。其注完全脱开了《道德经》辞句。劝人无心,不著名相,超然物外修大道。作者为茅山道士,全书以诗歌唱颂形式注解《老子》。经总序颂云:“紫雾光中信息通,聊将黄叶玩儿童。若拘语句明宗旨,辜负当年白发翁。”认为要理解《老子》的主旨,不在于字句的训诂,而在于靠直觉去“悟”。又第一章颂云:“绵绵密密绝胚胎,动着尘埃拨不开。今日为君通一线,一齐吹向此门来。”以气喻道,以胚胎喻人心。道无所不在又无可捉摸,人心中也有道在,只是被后天尘埃埋没,故不能得道。只要清静修炼,便能拂去尘埃,直见本心,独得妙悟,如风过穴,豁然贯通。可见南宋茅山道已深受禅宗顿悟说的影响。其诗颂注解形式在道教经典注疏、弘传中亦别具特色。
蒋融庵 · 著 -
明真破妄章颂
《明真破妄章颂》题“虚靖张真君著”。虚靖即第三十代天师北宋张继先。“玄”字不避讳,疑为元人依托。七言绝句43首。述雷法。以心为玄关,述先天祖炁和真阴阳,批评其它雷法皆为妄。
张继先 · 著 -
道德篇章玄颂
《道德篇章玄颂》题“新授郢州防御判官将仕郎试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宋鸾”序,称宋鸾撰本颂。“匡”字缺笔,宋鸾盖北宋人。以七言韵语注《道德经》81章大意,摘引《道德经》部分词句。颂文内容强调虚静并主张修炼长生。
宋鸾 · 著 -
庄子内篇订正
《庄子内篇订正》经名:庄子内篇订正。元人吴澄撰。二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
吴澄 · 著 -
文始真经注
《文始真经注》一名《文始真经直解》。道教经籍。南宋牛道纯撰。9卷。前有《关尹子》传略、《文始真经直解跋引》。以月照千江、因指见月的比喻来解说不可思议、不容言说的奥秘。以妙有真空的思想注解《关尹子》,每句都注,颇为详明。
牛道淳 · 著 -
二程遗书
《二程遗书》理学著作。宋程颢、程颐著,朱熹编。是程颢、程颐门人所记其师讲学的语录。二十五卷,《附录》一卷。二程死后,所传诸家语录散乱失次,并且各以己意,不能统一。朱熹家藏旧本,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头尾相贯,未经后人之手,最为精善。后又以类访求附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次,并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该书是二程门人耳闻目睹二程嘉言善行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二程人性论、天理论、本体论、格物致知论等思想体系。
朱熹 · 著 -
茅盾散文集
《茅盾散文集》散文随笔集。《茅盾散文集》毕竟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它是散文和杂文的结集。作者说,这些文章是被“逼”着写的,收集起来出版,也是因为书店要稿子,“拿这些来充数”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好书,在30年代产生过影响,也奠定了茅盾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郁达夫曾说: 茅盾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的所长。”到30年代,茅盾真正地按郁达夫的说法,“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写作了不少速写和随笔,成就了作为散文家的茅盾。待到1935年12月,茅盾编了散文的自选集《速写与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被列为“开明文学新刊”之一种,可见其成绩之斐然了。
茅盾 · 著 -
文始真经言外旨
《文始真经言外旨》道教经籍。南宋陈显微撰。9卷。《文始真经》即《关尹子》。作者认为老子之道,不可言说。而关尹请老子强为之说,必然言未尽意。关尹当为老子第一弟子,述成此书,以披露《老子》奥旨,其文可贵,然文约义丰,后世难知,故再阐述关尹之意。又认为《文始真经》九篇排列的次序,是说明“一化为九,九复归为一”的意思。作者弟子称此书“探老、关骨髓,述成言外经旨”,故名。
陈显微 · 著 -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
《不空罥索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一卷,唐不空译。自不空罥索神变真言经之第二十八卷抄译者。世所谓光明真言,即此中之陀罗尼也。
佚名 · 著 -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
《不动使者陀罗尼秘密法》一卷,唐金刚菩提译。明使者即遮那化身,能满种种愿,及证无上菩提.
佚名 · 著 -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
《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译曰步掷。金刚神之名也。有播般曩结使波金刚念诵仪一卷。
佚名 · 著 -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全一卷。为唐代不空(705~774)所译之密教经典。又作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毗沙门随军护法真言。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书乃叙述毗沙门天诸种成就法、毗沙门天王之咒及画像法、根本印、吉祥天女印、赞等,并引用四天王经,列举其念诵法及解秽陀罗尼。又其中诸成就法一段与多闻天王陀罗尼仪轨为同本异译。
佚名 · 著 -
冰揭罗天童子经
《冰揭罗天童子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内容述说冰揭罗天童子之念诵法、造像法、陀罗尼法、印契等。
佚名 · 著 -
燕都日记
《燕都日记》《燕都日记》系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以后冯梦龙的日记。日记环绕李自成进攻燕都,明王朝灭亡之故实,带及许多方面有关实况,其中若干细节,为一般正史所未详。
冯梦龙 · 著 -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
《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汉传因明著作,唐慧沼著。该著是对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要义诠释的汇集,对《因明入正理论》解题目在《大疏》五解的第三解下更助二解。对“能破定非似立、似破”、“本欲成法依有法,不欲成有法依法”、“显因同品”等作了专门的阐释。现存于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商务印书馆1923年影印出版。
慧沼 · 著 -
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丛话》南宋胡仔编。10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该书是在《诗话总龟》影响下编辑的,两者是姊妹篇,集中了北宋以前诗话的精华。在编排体例上,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对一些琐闻轶句采取分类附录办法,眉目清楚。凡属大家,均出其名,以年代为先后,把作家与作品、作品与本事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使文学流变的脉络清楚地呈现出来。于记事之外,兼重品评,学术性强。作者阅读面广,对于所辑录的材料经过严格选择,附有案语评议,申明自己的观点。纵横比较,眼界开阔。如论杜甫的诗学渊源、《杜鹃行》等,都能在充分引证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更为深刻、全面的看法。对杜诗出典、乘槎典故、韩愈《听颖师弹琴》、王建《宫词》中他人误入之作的探讨辨析,亦具此特点。这些问题往往是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公案,作者把主资料收集在一起,对研究者十分有用。作者独特的批评眼光还表现在能总结、点明诗歌本身的特殊规律,如对杜甫律诗变体、律诗扇对格的界定、分析皆令人信服。书中还经常引用三山老人(作者的父亲》语录评论某一诗人或作品,亦多精见,如论杜甫五言排律腾挪跌宕的格局、论《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深刻寓意等等。作者论诗,推崇李杜,认为他们都是集大成者。此外还收有
胡仔 · 著 -
因明义断
《因明义断》佛典注疏。唐慧沼撰。一卷。是《因明入正理论》的论释书。旨在辨析诸家有违本论宗旨的言论,同时宣扬初祖窥基之说。慧沼另撰有《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一卷,阐发本书未涉及的论点。见载于日本《大正藏》。
慧沼 · 著 -
薛氏集异记
《薛氏集异记》小说。唐薛用弱撰。二卷,又作一卷或三卷。用弱字中胜,河东(今山西)人。长庆、太和时曾任光州刺史等职。是书所记多为隋唐时奇闻异事,主人公多为士人、诗家、释道者流。故事情节完整,亦较曲折,有形象刻画,叙述颇具文采。如王积薪妇姑对弈、狄仁杰赌集翠裘、王维奏“郁轮袍”曲、王之涣三诗人旗亭画壁诸故事等等
薛用弱 · 著 -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
《佛说顶生王因缘经》宋北印土沙门施护等译,佛在祇园,因胜军王请问,为说往昔修布施行。从王顶生,乃至统四大洲,诣忉利天,总经一百十四帝释谢灭。
佚名 · 著 -
四分戒本疏
《四分戒本疏》又名《四分律戒本疏》、《四分戒疏》。佛教戒律注疏。作者不详。或首题:“沙门慧述”。四卷。北图有藏12等三十七号,其中不少卷子首尾可相接。英法等国藏有S.1144、P.2064等近二十号。《敦煌劫余录》谓:此文“与唐法砺所撰之《四分戒本疏》互校,文句虽有出入,意旨要自不殊。考《续高僧传·法砺本传》:‘讲律临漳,休与有功。’《慧休本传》亦云:‘尝听砺公讲律。’此疏或即慧休法师听讲时笔录。而今藏本殆后人依据慧师所录,增益而成耶?”此文分门与法砺疏同,内容亦较接近。但沙门“慧”是否名“慧休”,或“慧述”本身即为人名,待考。此文与法砺疏是何关系尚需研究。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卷一、二、三等三卷收入第八十五卷。
佚名 · 著 -
性命古训辨证
《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著,1947年商务印书馆版,分上下2卷,共22章。辨证了周代金文中生、令、命三字之统计及字义;《周诰》中性字、命字;《诗经》、《论语》、《左传》、《国语》中之性字、命字;告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言性之本原及区别;生字与性、令、命诸字之语言学关系;阐释了周初人之帝、天、天命无常之义;诸子天人论道源;自类别的人性观至普遍的人性观;《墨子》非命论;汉代性之二元说,理学之地位。本书是为辨证阮元《性命古训》而作,对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傅斯年 · 著 -
大乘四法经释抄
《大乘四法经释抄》大乘四法经释抄,一卷,佚名,编号二七八四。
佚名 · 著 -
庄子解
《庄子解》解说《庄子》一书的著作。中华书局1964年本,1册,33卷。王夫之著,王敔《增注》,王孝鱼整理。此书说解《庄子》,注重其思想内容及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综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后,加以解说,以描述庄子的思维过程。王氏认为《寓言》和《天下》乃全书序例,非庄子本人不能写出,内篇亦出庄子之手。对杂篇《庚桑楚》尤为重视,以为庄子基本思想已囊括其中。《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定为赝作,屏不解说。至于各篇中单词句义,也往往有新的解释。此书评《庄子》,志在除去前人以儒佛两家所作的附会,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同时还隐为指出其局限。王敌对本书的《增注》,引用古今各家之说颇多,对明代名著,亦偶有采录。此书整理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参校湘西草堂本。书前有点校说明,以及清王天泰、董思凝的两篇序言。
王夫之 · 著 -
论道
《论道》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金岳霖 · 著 -
新庵译屑
《新庵译屑》《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署“上海新庵主人译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1908年9月),吴趼人应周桂笙(即新庵主人)之请,为之编辑并作序。并将周桂笙原为《知新室新译丛》所写《弁言》置于卷首。但当时并未以单行本出版。吴趼人去世后,周桂笙大约又增加了若干篇目,计得九十题九十四篇,与其所著《新庵随笔》合编为一册,合称《新庵笔记》,其中卷一、卷二为《新庵译屑》上、下,卷三、卷四为《新庵随笔》上、下,并增任堇《序》一篇,于1914年8月由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 《新庵译屑》所收作品来自四个部分: (一)《知新室新译丛》,共计二十篇,全部入选《新庵译屑》。 (二)《新庵译萃》,共计六十七篇,入选《新庵译屑》者五十九篇。 (三)《自由结婚》,同题四篇,均入选《新庵译屑》。 (四)散作十题十一篇,除《俭德》一篇选自《新庵随笔》外,未见在报刊上发表,可能是周桂笙新增译作。 在《新庵译屑》九十题九十四篇译作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二篇。此外,原《新庵译萃》中有一篇《欧洲糖市》,也附吴趼人的评语,而《新庵译屑》漏收,今为之补入。如此,《新庵译屑》总计为九十一题九十五篇,其中吴趼人加评者三十三篇。
吴趼人 · 著 -
律戒本疏
《律戒本疏》律戒本疏两种各一卷,一,首缺,北周玄觉题记,编号二七八九。二,首缺,西魏昙远题记,编号二七八八。
佚名 · 著 -
先秦学术史
《先秦学术史》收录傅斯年有关先秦学术研究的相关内容。主要内容包括:战国子家叙论、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社会的缘故、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等内容。
傅斯年 · 著 -
律杂抄
《律杂抄》律杂抄,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〇。
佚名 · 著 -
小经理
《小经理》现代短篇小说。赵树理著。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列入“大众文艺小丛书”。作品描写了解放区供销合作社新旧人物矛盾和斗争的故事。三喜“从小就是个伶俐的孩子”,但是“因为家穷”,“没有念过书,不识字”,“长大了不甘心,逢人便好问个字”,“也认了好几百”。1942年减租减息后,他在与合作社旧经理、原来的高利贷者张太的斗争中,表现积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群众推选他任合作社经理。当上经理后,三喜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克服缺少文化的困难,掌握了合作社的业务知识,战胜了思想上还没有转变过来的掌柜王忠的捉弄和刁难,如磨洋工、装病等,办好这个小小村的合作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经理。小说以通俗、形象的语言,简短的篇幅,表现了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人。
赵树理 · 著 -
陶甓公牍
《陶甓公牍》晚清徽州知府刘汝骥所编撰,清宣统辛亥(1911)夏安徽印刷局校印,刘汝骥在晚清新政时期组织对徽州进行社会调查的文献汇编,凡十二卷:卷一“示谕”;卷二至卷九“批判”,包括吏科、户科、学科、兵科、刑科、工科、宪政科等;卷十“禀详”;卷十一“笺启”;卷十二“法制科”,包括民情习俗、风俗习惯、绅士办事习惯等。内容涉及晚清徽州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具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徽州乃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翔实而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刘汝骥 · 著 -
实干家潘永福
《实干家潘永福》赵树理著。发表于《人民文学》1961年4期。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潘永福是山西沁水县农民出身的干部,参加革命前热心为群众办事,又有熟练的生产技术,深受群众爱戴。参加革命后当了农村干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作品着重表现他在1959年和1960年办农场、修水库等工作中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作风。尤其在经营管理上,讲究实际,精打细算,管理有方。作品选择人物一生中的若干典型事例,热情歌颂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无产阶级实干精神,是对当时“浮夸风”的有力批判。小说一发表,是一篇切中时弊、醒人耳目的优秀之作。
赵树理 · 著 -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
《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宗四分比丘随门要略行仪,一卷,首缺,编号二七九一。
佚名 · 著 -
地持义记
《地持义记》佛典注疏。作者及原经卷数不详。似为五卷。首残尾存。尾题“《地持义记》卷第四。沙门善意抄写受持流通末代。”是对北凉昙无谶译《菩萨地持经》的疏释。现存残卷自卷七“云何菩萨四无碍慧”疏释至卷八《法方便处菩萨相品第一》末。因卷一佚亡,故科分不清,但释义精辟扼要,研究者或谓作者受真谛译《大乘起信论》影响。据《新编诸宗教藏总录》,隋慧远撰有《地持经义记》十卷,今唯存三卷,已编入日本《卐字续藏》,但与此《义记》不同。历代大藏经未收,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佚名 · 著 -
三部律抄
《三部律抄》三部律抄,一卷,首缺,旷许题记,编号二七九三。
佚名 · 著 -
后山谈丛
《后山谈丛》四卷。宋陈师道 (1053—1101)撰。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 (今江苏徐州)人,博学精深,熟通诸经,喜作诗,与苏轼、黄庭坚、秦观、张来、晁补之、李荐并称“苏门六君子”。由苏轼等荐为棣州 (今徐州)教授,徽宗时,官至秘书省正字。著有《后山集》、《后山谈丛》、《后山诗话》传于世。此书陆游《老学庵笔记》疑为后人伪托,或以为是其少时所作。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考证: 陈师道《后山集》前,有其门人魏衍附记,称 《谈丛》、《诗话》别自为卷,故此书确为陈师道所作。此书所记皆宋代政事、边防、朝野琐事、文人轶闻等,共二百七十一条,对研究宋史有一定参考价值。文笔简洁高古,颇具文学性。有 《四库全书》本、《宝颜堂秘笈》本、《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后山集》后附刊本。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伟国点校本,与 《萍州可谈》合刊。
陈师道 · 著 -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
《十六大罗汉因果识见颂》天竺沙门阇那多迦译,范仲淹序,其内容乃十六国大阿罗汉为摩拏罗多等诵佛说因果识见悟本成佛大法之颂偈颂皆押韵语义俱妙。经首有对“因果识见”的题解: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识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若因缘有善果报有福则自识其本心见其本性使万法不生当得成佛。
佚名 · 著 -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
《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全一卷。唐代不空译。又作大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无障碍经、莲华三昧经。收于卍续藏第三册。本经系以密教观点来解说妙法莲华经,全经以金刚萨埵之请问及大日如来之答说形式所成。其内容,初举‘归命本觉心法身’等二颂八句之本觉赞;此赞偈颇为著名,被视为古来三世诸佛随身之偈,又为一切众生成佛之文。次述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前十四品以文殊为本尊,后十四品以普贤为本尊之义,并阐说五重、九重之普贤。其后又于方便秘密三摩耶品、见宝塔秘密三摩耶品等诸品之中,分别宣说‘十如是’与‘八叶九尊’之配当方法、宝塔与法华经根本一字阿字之深旨、提婆达多之本源、龙女及草木成佛之密咒、久远实成如来之尊形、心真言、住所,与常不轻菩萨礼拜之意义等。
佚名 · 著 -
甲申纪事
《甲申纪事》记录明末史事的丛刻,又名为《甲申纪闻》。明代冯梦龙辑。共十三卷,附录一卷。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城。紧接着,明朝残余势力又拥戴福王朱由崧登基,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同年九月,“九王子”顺治帝从沈阳迁至北京,将北京定为清朝首都。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将近二百七十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关于这一年的史事,有许多文人墨客对其挥毫泼墨,有的记叙当时事变的过程,有的记录明亡时诸大臣的各种言行,还有的搜集各种轶文怪事敷演为文。冯梦龙的《甲申纪事》便是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当然,其中也有两卷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而成的,如第二,第三卷。
冯梦龙 · 著 -
书集传
《书集传》《尚书》学著作。宋蔡沈所作《尚书》注本。六卷。蔡从学于朱熹,朱熹死前一年命蔡作此书,故书中不少地方融进了朱熹的学说成果。其自序说:“沈自受读以来,沈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三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志别。”该本遍注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并于篇中分别标明今文古文的有无,改正《孔传》的训诂。疏通证明,比孔颖达疏简易清晰,且大体精当。元代将此书与古注疏并立学官,而独此书倍受士子青睐。明代永乐年间,胡广奉敕撰《书传大全》,用《蔡传》为主,此后,一直用作试士的标准注本,直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时。该书于宋理宗淳祐(1241——1252)年间由其子蔡杭进于朝廷时,附有《小序》一卷,专门辨驳百篇《书序》的讹误。元末明初的刊行本尚连《小序》,然《宋史·艺文志》所著录者亦止六卷,似不包括《小序》。有《四库全书》本。
蔡沈 · 著 -
德育鉴
《德育鉴》近代梁启超编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作为《新民丛报》临时增刊发行。分《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其重点在《知本》一章。认为“道德之根本则无古无今无中无外而无不同”,“道德者,不可得变革者也”(《德育鉴·例言》)。在道德修养方法上批评朱熹而推崇王守仁,认为“朱子之大失,则误以智育之方法为德育之方法”,是“头痛灸头,脚痛灸脚”,抓不住根本,终无收效之期(《德育鉴·知本》);王守仁专主“致良知”,是“专治病根”,可以收到“一了百了”的效果。宣称“致良知”说“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同上)。认为“今日求精神教育”时“惟有奉阳明先生为严师”,以王学为“独一无二之良药”(同上)方可。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专集》第6册。
梁启超 · 著 -
至大金陵新志
《至大金陵新志》元南京都邑志。十五卷。元张铉撰。刊行于至正四年(1344年)。该志采用纪传体,分为图考、通纪、世表、代表、志、谱、列传、摭遗、论辨。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表、志、谱、传“以及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摭遗论辨“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文摭其实,事从其纲”。卷一,地理图。卷二,金陵通纪。卷三,金陵表。卷四,疆域志。卷五,山川志。卷六,官守志。卷七,田赋志。卷八,民俗志。卷九,学校志。卷十,兵防志,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古迹志。卷十三,人物志。卷十四,摭遗。卷十五,论辨。
张铉 · 著 -
诗经世本古义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楷字元子,镇海卫(今属浙江省)人。楷博综群书,尤邃经学。天启进士。值魏忠贤乱政,不谒选而归。崇祯间迁科给事中,举劾无所避。杨嗣昌夺情入阁,楷劾之,忤旨贬二秩。福王命掌都察院,几为忌者所害。漳州破,抑郁而卒。着有《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是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故名曰“世本古义”。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三代有诗之世,凡二十八王,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凡名物训诂,考证详明,典据精确,有可取之处。然于史实颇多舛误,读者当引以为鉴。是书有清嘉庆二十四(1819)年谢氏刻本。清徐时栋校并跋,另有《四库全书》本。
何楷 · 著 -
雨山和尚语录
《雨山和尚语录》二十卷,清上思说,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七世,嗣巨渤恒。卷第一住庐山镜湖院语,卷第二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三住延令庆云寺语,卷第四住东鼓法轮寺语住龙舒白云院语,卷第五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六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七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八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九住如皋大觉院语,卷第十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一住昭易极乐院语,卷第十二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三住海虞三峰清凉院语,卷第十四住维扬天宁寺语,卷第十五机缘,卷第十六颂古,卷第十七诗偈,卷第十八法语书问,卷第十九杂着,卷第二十佛事。
雨山上思 · 著 -
清河书画舫
《清河书画舫》十二卷。中国书画著录书。明代张丑撰。丑生平在《张氏书画四表》中著录。此书成于明万历四十四年,取黄庭坚“米家书画船”诗句意为此书名。前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严诚序及例略。卷一至卷二为三国、晋(莺字号、嘴字号),卷三至卷五为南北朝、唐、五代(啄字号、花字号、红字号),卷六至卷十一为宋元(溜字号、燕字号、尾字号、点字号、波字号、绿字号),卷十二为明(皱字号)。全书共收自晋钟繇至明仇英一百四十家。其中书家包括少数书兼画家共七十人左右,书画几乎各占一半。以书画家为纲,以其书画作品流传者为目。首列真迹,次采与真迹有关之题跋等,各注所出。其题跋有录自真迹,有录自书画史、书谱、书品、题跋、著录及各家文集,有据传闻补入。均为有作者生平、作品的形成、品评、流传、递藏、鉴定等方面的内容。时有张丑进行评论及考证的按语。所采详备,考证亦精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如《宋史·米芾传》载米芾卒年四十八,而米芾尚有四十八岁以后所作真迹流传;张丑据此考证,认为米芾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大观元年(1107年),年五十七,恰与米芾印迹“辛卯米芾”相合,足补《宋史
张丑 · 著 -
丽情集
《丽情集》宋代文言传奇小说集。北宋张君房纂辑。是书专录“古今情感事”,故名。原本二十卷,《郡斋读书志》著录,今已佚。《类说》、 《绀珠集》均收有此书,但均为摘引片断, 不是原文。宛委山堂本《说郛》所收,与《绀珠集》大致相同,似即据后书转录。今人程毅中撰《〈丽情集〉考》, (刊《文史》十一辑),以《类说》本为基础,广征宋、元、明人著作,辑考此书的篇目、本事、作者及出处等,共得三十八篇。
张君房 · 著 -
蕉庵诗话
《蕉庵诗话》魏元旷的《蕉庵诗话》及其续编在民族意识领域总体以满汉民族关系探讨为中心,围绕社会鼎革导致的遗民思想与遗民意识内容,具体落脚在以下方面:称颂遗民节义,斥责临危易主、变节之人,记录变名、易服、复辟之故事,蕴归隐之志,以史笔载录诗词,以春秋笔法展现"孤露遗臣"之情怀。这种"关乎时政"的特征固然与诗歌理论的贫乏有关,但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鼎革下作者的民族情感变化及在社会转型中的心态。
魏元旷 · 著 -
献贼纪事略
《献贼纪事略》作者无名氏。不分卷。本书主要记述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事迹,对其起义始末记述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大西军的重要资料。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整理本。
佚名 · 著 -
千金宝要
《千金宝要》医方著作。6卷。唐孙思邈原撰,宋郭思编纂于宣和六年(1124年)。此书乃选取《千金方》中部分医论和有效单方,使人知防病于未发之前及已病后治疗之法;并附有郭思及他人效方。分妇人、小儿、中毒等17篇。为使之广泛流传,宣和六年(1124年)刻碑于华州公署;迄明景泰六年(1455年)杨胜贤以石碑于冬月不便摹印,始易刻木板印行。明隆庆六年(1522年)秦王守中喜其方之简便,药之近易,鉴于天下之游耀州真人洞者,岁无虚日,日无虚时,因刻石于洞前。其碑现仍完整珍藏陕西耀县药王山真人洞前千金宝要碑亭内。现有明隆庆六年刻石之拓本及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后的近10种刊本、石印本。
郭思 · 著 -
续通典
《续通典》中国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间,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影印精装1册。本书为《通典》之续书,共150卷,分类大致与《通典》相同,仅把兵与刑分列,计为9典。包括《食货典》16卷、《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4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14卷、《州郡典》26卷、《边防典》4卷。记载唐至德元年(757)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以明代典制为最详。资料除来自正史外,还引用了《唐六典》、《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山堂考索》、《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典章》、《明会要》、《明集礼》以及唐宋元明各代文集、奏议等。资料较为丰富,编排亦较条理,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书内容与《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有些重复。
多人 · 著 -
温疫论
《温疫论》《温疫论》亦作《瘟疫论》,系温病专书。2卷,补遗一卷。明·吴有性撰。书成于1642年(崇祯15年)。书中讨论瘟疫证治,吴氏谓“温”、“瘟”二字没有区别,都属于温热病范围,因以“温疫”名书。书中阐明了瘟疫与伤寒相似而迥殊的新见解,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又称疠气、戾气)。指出瘟疫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又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如脉、舌等的不同),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创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剂予以调治,开后世治温疫一大法门。原书2卷未多加诠次,很象是随笔记录而成。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曰:“瘟疫一证,始有绳墨之可守,亦可谓有功于世矣。”同时指出书中不足为:“其谓数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伤寒;数百伤寒之中,乃偶有一阴证,未免矫枉过直。”该书问世后,流传甚广,康熙年间日本即有刊本,国内翻刻本及阐释发挥之书甚多,建国后有多种铅印书及评注本。
吴有性 · 著 -
现报当受经
《现报当受经》佛教经典。著译者不详。一卷。本经的主旨是讲罪业报应。谓一妇人因嫉妒,杀害妾生之子,后世得种种恶报。又因曾解衣带布施辟支佛,故后值佛拯救。此经最早见录于《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被判为伪经,故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中有收藏,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是否疑伪经尚需研究。
佚名 · 著 -
像法决疑经
《像法决疑经》中国人假托佛说所撰经典。作者不详。一卷。本经谓如来应常施菩萨所问,回答未来像法世界中众生作何福德最为殊胜的问题。认为应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及至饿狗,提出布施更胜于敬佛法僧三宝,为六度之首。经中对像法期中,僧俗人等的造恶及佛法的颓废作出种种预言,谓善必有恶,盛必有衰,虽佛法亦不能免。最后谓未来世四辈弟子能于本经生欢喜心,所得功德无量无边。本经最初见录于《法经录》,被判为伪经,但后世亦有人持不同意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遗书有收藏。日本曾据传入的经本收入《卐字续藏》。敦煌出土后,又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
佚名 · 著